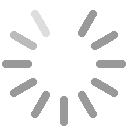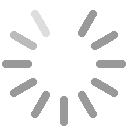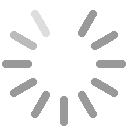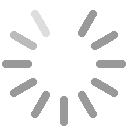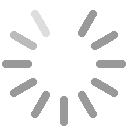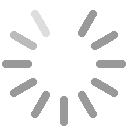张海儿作品,他说:“普通人眼中的坏女人,就是我眼中的好女人”
这是我考量别人的作品时心里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。当编辑们做一个选题时,我总是问他们有没有“由头”。也就是说,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选题,而且是在“此时此刻”做这样的一个选题?他们回答:哦,因为明天是约翰-列侬多少周年纪念日;我们正在经历月全食……那么,好,执行吧。
拍照片需要理由吗?如果我们这样问的话,那么那些手持相机,并试图获得快乐的人必然要报以怒色,他们似乎从没想过这些事情。但从摄影术诞生的那天起,摄影就决定了摄影必然要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。
“摄影如奇遇”。这个奇遇一定是以时间为标记,奇妙地发生。
南•戈尔丁曾经自拍被男友暴打瘀青的脸,是源于女性的反抗意识;戴安•阿勃丝之所以拍那些侏儒、变性人和畸形人,与她出生于优裕家庭所携带的那份孤独感不无关系,她通过作品与他们建立关系,进行交流。
以搭建场景进行“造相”而著称的艺术家贝尔纳•弗孔,用人造模特儿来大量拍摄儿童嬉戏场景,这是源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向往,他在自述第一张“造相”作品诞生时如此说:“在1976年的春天,第一个影像基本形成了,在我房间一个墙角,一个真的戴着金色头发的头亲吻着一个模特儿的头,透过一束假花”,这显得魅幻又真实。而他在结束了自己的摆拍生涯时又如此说:“我20年的重新拾回的天堂,为了证明这所谓的第二个天堂及摄影的天堂,这个在童年遗失的天堂,现在也丢掉了。”此刻,摄影于弗孔,就是为自己生命给出一个理由,用它来获取对童年丰杂岁月的惦念与再现。
有理由,而且是内心生发,不可不说,直至水到渠成。就像地下室之于简•索德克,阳子之于荒木经惟,“坏女人”之于张海儿,西海固之于王征,三峡之于颜长江,同性恋之于韩超,左手之于右手,柔情之于爱怜。
某种程度上,理由就是血缘和命运,这血缘和命运百转千回,扭捏酝酿,直至灵魂附体,没有血缘的介入就是干涉,有了血缘,那命运就是自己的。
我们不妨提更多的问题给自己,比如说,为什么别的地方好好的不拍,你偏偏来拍新疆?或者西藏,或者西海固,或者坝上,或者其他地方?这个地方与你什么关系?你了解那些人吗?你得到了什么?你的表达与那个地方距离有多远?你真正地感知过那个地方吗?
换个角度,假如我们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,翻开拍摄的那些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的照片,我们努力去寻找大脑中那些能与照片联系起来的东西,但觉得吃力,并且不是滋味,那么,这个时候,快乐就只是个简单的幻觉。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,因缘际会造成相识,而从陌生人到相熟,中间隔着的,就是理由。
摄影,未尝不是如此。